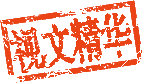|
天边几个移动的墨点,衬着晴朗的天空,格外分明。近了,才看清那宽大翅膀下雪白的覆羽,像暗夜撕开几道耀眼的口子。飞是沉静的,双翅平展,几乎不见扇动,只借着山谷里早起的气流滑翔。那姿态里有种天生的、不容置疑的庄严,仿佛它们不是来觅食,而是来赴一场神圣的晨会。 领头的那只率先收拢翅膀,铁锚般落在一块沙洲上。随后,十几个身影次第降落,长腿如两根朱红的细竹,稳稳扎进浅水里,激起几圈涟漪。它们站定了,并不急于动作,只是昂着那墨玉般的颈项,用红宝石般的眼,静静地环视这片尚在苏醒的领地。一时间,河滩上立起了一片沉默的、黑曜石雕成的林。 静默里藏着秩序。短暂的肃立后,队伍便自然散开了。它们彼此保持着恰当的距离--那是一种既互不干扰,又能遥相呼应的默契。一只踱向水流舒缓的回湾,那儿的水草丰茂,是鱼虾藏身的温床;另一只走向卵石密布的浅水,也许那儿有螺蛳或水生甲虫。它们行走的姿势是审慎的,每一步都提起得极高,落得极轻,仿佛怕惊扰了脚下水做的梦境。 觅食的姿态各不相同,却共享着一种沉浸的专注。回湾处的那只,已然进入了禅定般的状态。它细长的腿浸在碧清的水里,水波漾着它火焰般的胫骨。它歪着头,目光如锥,死死锁住水下某处游移的暗影。阳光穿透水面,在它漆黑的羽毛上映出变幻不定的、孔雀尾翎似的幽蓝与铜绿光斑。世界对它而言,浓缩成了眼前那方寸之水。忽然,那曲着的颈弹簧般弹射出去,长喙刺破水面,“啵”一声清响,快得只在视网膜上留下一道模糊的黑色闪电。再抬起时,喙尖已衔着一尾银亮的小鱼,鱼尾徒劳地拍打着空气,溅起几点细碎的水星。它并不急着吞下,只将头颈优雅地一扬,让那银光在空中划出一道小小的弧线,调整到顺喉而下的位置,方才咽下,喉部有一个满足的、不易察觉的蠕动。 这觅食的图景里,也有无声的交流。一只捕到稍大些的猎物,附近的同伴便会暂停自己的动作,微微侧首,投去短暂的一瞥,那目光里没有嫉妒,更像是一种平静的见证。偶尔,两只觅食的范围有所重叠,其中一方便会不声不响地、略带歉意似的后退几步,转向另一片水域,仿佛遵守着一条古老而绅士的协定。 太阳渐渐升高了,将它们的影子拉得细长,投在粼粼的水面和金黄的沙地上。吃饱了的,会踱到沙洲高处,单腿而立,将长喙埋入胸前的羽毛,闭目养神。那副模样,像极了饱读诗书后倚着书案小憩的文人,餍足而安详。还在忙碌的,依旧不慌不忙,沉浸在与水、与鱼、与这片河滩的私密对话里。它们的羽毛在正午的强光下,黑得愈发纯粹,白得愈发耀眼,宛如一组散落在自然画布上的、对比强烈的音符。 我忽然明白了它们自由自在的底蕴。那并非放纵不羁的狂欢,而是一种深深植入环境律动的、高度自律的和谐。每一只黑鹳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片河滩上的位置与角色,知晓食物的所在,也尊重同伴的领域。它们的自由,是在对河流法则的谙熟与恪守中获得的。那是一种沉静的、专注的、与天地共呼吸的自在。当它们展开宽大的翅膀,陆续飞离这片丰饶的浅滩,重返青空时,身后留下的,不仅是被梳理过的、重归平静的水面,更是一种关于生存之道的、庄重而优美的诠释。河滩空了,却又仿佛被某种充实而安宁的东西永久地填满了。
本帖最后由 陽光 于 2026-1-19 07:37 编辑
|